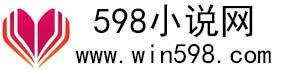22-30(34/44)
一番昨日记忆,断档在沈砚抱她走去床榻之前。之后发生了何事,她一丝一毫都不记得。
现如今她整个人牢牢裹在被褥里,衣衫已被汗濡湿。
“……奴婢去瞧一瞧药有没有煎好。”
“……奴婢去给姑娘取一套能换的干净衣裳。”
宁沅尚处在刚醒的茫然里,见房间内只余沈砚与自己两人,下意识道:“对不起,我没有要搅扰你好事的意思。”
沈砚不解:“什么好事?”
宁沅咽了咽唾沫道:“……调戏女使。”
“我都看见了……她们的脸都红了。”
沈砚艰难阖了阖眼。
这女人活在世上,大抵就是为了气他。
“她们是被你调戏走的。”
她讶然道:“怎么可能?我才刚醒……”
他冷哼一声:“是啊。”
“就你在梦里喊,什么扒衣裳,什么死变态……还不知道在冲谁撒娇。”
“旁人到底也是未嫁的姑娘。”
说到这儿,他故意叹了口气,惹得她更添愧疚,而后顿一了顿,明知故问道,“宁小姐,你梦见的是谁啊?”
“没,没谁。”
她别开眼,不敢吱声,掩在乌发下的耳根可耻地红了。
救命,她怎么总梦见沈砚!
且梦里的他一次比一次离谱。
思来想去,大抵是他们二人日渐亲密之故。
上回她在客栈外气急败坏,亲了他一口,后来便梦见她在梦里和他亲吻。
昨夜她中了催情。药,后来便梦见他俩这样那样,是不是说明……
该发生的,已然发生过了?
她试探问沈砚道:“那个,我的催情。药可解了?”
说起这个,沈砚便很是无语。
为什么会有人连自己是发烧还是中药都分不清楚?
人在无语至极时真的会笑。
他轻笑一声,道:“你说呢,宁小姐?”
“你自己身子究竟如何,你自己都不知道?”
她如今身子不烫了,头也不晕了。
想必那催情。药已然解了。
……可恶,她怎么又是没有丝毫感觉?
明明话本里写过,未经人事的少女初尝禁果后都会腰酸腿软,身子疲累。
她怎么觉得她除了有些热,反而神清气爽?
而且那过程里的充实与骤失她也丝毫不曾感受过。
“……我记得后来我好像晕过去了。”她语气温吞,换了个更委婉的问题,“那之后……咱们在公主府留了多久呀?”
“不久,大约一盏茶罢。”他随口道。
宁沅心下一惊。
这么快!
难怪她没什么感觉!
宁沅自诩杂家,博览群书,心中自然明白,欢好与亲吻的区别很大。
亲吻只看技巧与情意,只要这二者到位,任谁都能飘飘欲仙。*
至于欢好是否能得到良好的体验,外在条件才最为紧要。
她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向沈砚革带之下的白袍,心中稍有叹惋。
沈砚对她的心声愈发无语。
她就不能把他往好处想?
想他其实是个正人君子,按捺了不轨之心,并没有碰她吗?
他冷睨她一眼,道:“你看什么?”
好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