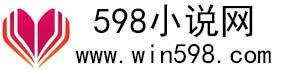24-30(2/24)
目光在她膝上的暗红处略停,眸色微沉,将人抱得更紧些,“要干什么,想干什么,便说一声,不是最爱使唤某么?别省着,某,心甘情愿被你使唤。”崔竹喧象征性地推搡了下,便结结实实地攀住了他的脖颈,是他上赶着要这样的,又不是她主动向这个匪寇低头,再说,她确实走不动了。
她靠在他的肩上,眸光无处可去,便落在他的脸上,又或者说,是那几根指印和爪痕上,瞧着也不是很深,应当不会留疤吧?可她又不是故意的,谁让他突然变出个水匪的身份吓唬她。
只是她怎么也想不明白,为何,他会是匪?
她是这么想的,也便这么问了,可那人并不应声,转而提起了今晚的事,“发生什么了?”
不提还好,一提,崔竹喧那忍了一夜的泪水便决了堤,仅是几个呼吸间,就淋湿了他肩头的布料,“那个酒鬼突然闯到家里来,也不知道发得什么疯,非说我勾引他,我拿出你的名号吓他也不管用,就只能一个劲儿地逃跑——你还是水匪头子呢,连个酒鬼都吓不住!”
“都怪你!”
“嗯,都怪某。”
“我要扣你一大笔酬金!”
“好。”
几乎是崔竹喧说一句,寇骞便应一句,甭管是什么鸡毛蒜皮,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,都要被牵扯进来,变成责怪他的理由,诸如绊倒她的水坑,溅到身上的泥点,割破皮肉的碎石,乃至夜里转凉的风,天上不够明亮的月,都是寇骞的错,都该由他负责。
于是,过错多至罪不可赦的寇骞,便只能寻些法子讨饶,“某让小祖宗再打几下出气?”
崔竹喧瞥了眼他腰间挂着的砍刀,上头的猩红未干,她的声音不免有些发紧,“那、那你不许还手,不许躲,更不许记恨我!”
“好,”他仍是好脾气地应了,只是小心翼翼地补充了句,“商量一下,别打脸?”
没得到回答,寇骞不由得怀疑是不是自己提的要求过分了些,于是又继续退让,“那,要打也成,别当着旁人的面?”
崔竹喧依然不做声,寇骞叹了口气,彻底放弃挣扎,“行,小祖宗想怎么出气都行。”
话音刚落,肩上就传来一阵钝痛,他倒吸一口凉气,拧眉看去,是小祖宗在啃他。
可很快,她就松了口,往旁边“呸”了两声,抱怨他的衣料粗糙,又苦又涩,还硌牙,寇骞只能为让她下嘴更舒服些而提出建议,“……那你把衣领扯开来咬。”
夏日的衣衫拢共也没几层,崔竹喧一手环着他的脖颈,一手拽着他的衣领,在他的刻意配合下,轻而易举便见着了裸露的肩颈,上头横陈着深浅不一的疤痕,而现在,又添上一圈牙印。
平齿和尖牙齐齐陷进皮肉,疼倒是其次,湿热的舌不经意间舔舐时带起的一点痒,才最是叫人难熬,他下意识地绷紧了全身,连圈住她腰身的手也跟着紧了些,这种感觉无疑是难受的,可他一时竟分不清,到底是盼着她松口,还是,期望她咬得再更重些。
大约是是在腥甜漫溢至唇齿间,崔竹喧才恍然回过神,慌忙松口,就见一道血淋淋的印子,瞧着骇人得很,她不免有些心虚,将衣领草草拉回去,将罪证掩盖住。
她的脾气好像是有些坏了,天可怜见,她往日也没有打骂下人的习惯啊,怎就鬼迷心窍地朝他肆意撒气?
可能是因伤口泛疼,也可能是因为别的,寇骞的声音带着一点哑意,“现在高兴点了吗?”
“还、还行吧。”崔竹喧含糊其辞地回答,伏在他肩上,恹恹的,但好在,没继续哭。
逃跑时长得仿佛望不到尽头的路,